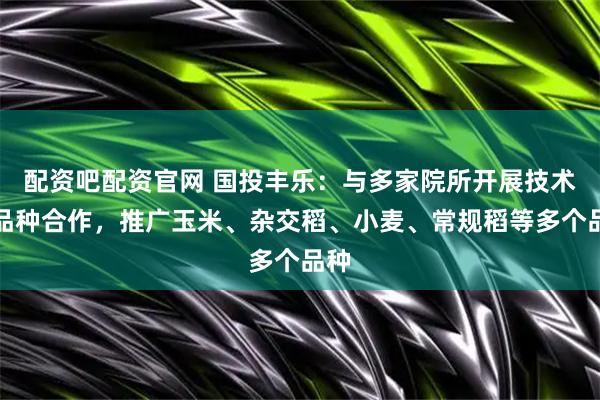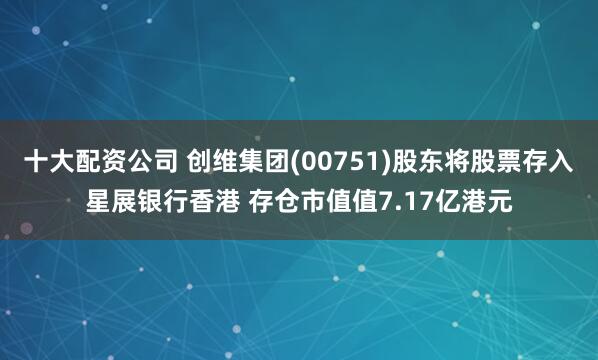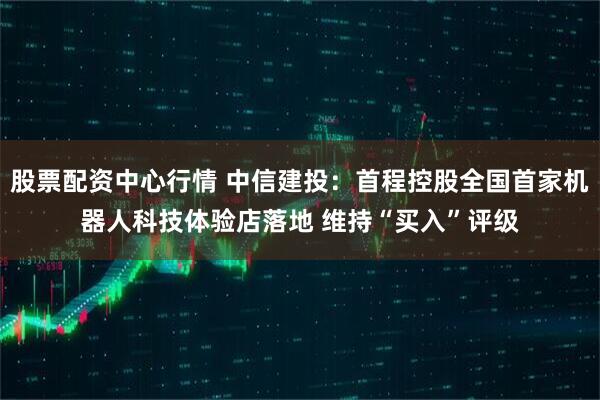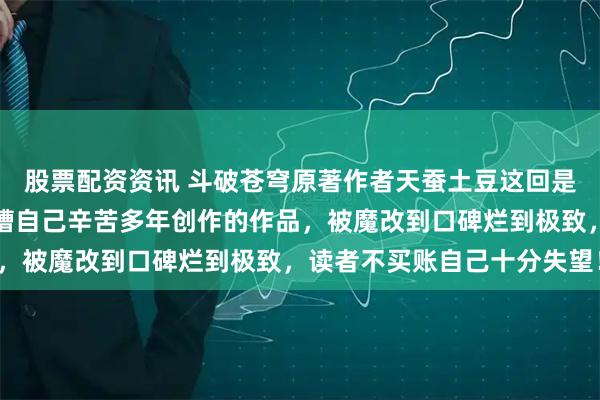王颂馀先生拜师求学二三谈(之二)炒股配资论坛大全
作者 喻建十
写在前面的话:今年是先外公王颂馀先生(1910-2005)去世二十周年,按照传统习俗,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为先人做点什么。现仅就我所知,介绍一下他拜师求学的一些往事,也算是些许纪念吧。
前文说过,王洁尘喜好书画,正是受父亲的影响,先外公自幼就开始了书画的学习。
在书法方面,他5岁习书,15岁时起跟随津门名家张寿(注:1877—1947 ,字君寿,号铁生,天津人。清末民国时期国学家。擅长诗文书法,富于文物收藏,精于文物鉴赏,通晓各种书体,尤以隶书、行书驰誉书坛。其隶书以汉隶筑基,汲取晋碑、魏碑笔法,贯通宋元意趣,形成自家法度。其行书锋芒峭劲,神韵飞扬,深得宋代黄庭坚、米元章书风之精奥。)学习书法。20世纪20-30年代在康有为崇尚北碑思潮的影响下,张寿以碑书风格名重津门。在这样一位老师的指引下,颂余先生开始临习《张猛龙》、《苏孝慈碑》,进而再临《张迁碑》、《天发神忏碑》、《龙门二十品》,并对文征明小楷情有独钟。由此得知,颂余先生在习书之初,并没有按照那时人们通常从唐楷入手的习书惯例。这无疑为我们理解他最后书法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先外婆曾说过外公十岁出头时就受人之托,题写了在当时算是高档社区的“效康里”(当时的法租界,现哈尔滨道靠南京路侧商圈)的匾额(这个牌匾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才遭毁坏)。
展开剩余88%与此同时,他在绘画上又先后拜李石君(注:1867-1933,名明起,以字行,四川雅安人,光绪拔贡,官凤阳知县,同知衔江苏候补道,又官福建,后任奉天盐务局文案,定居天津;指画大师,山水花鸟皆精,师法高其佩,作品酣畅淋漓而自出新意,清淡高雅,飘逸超脱,画风独具,炉火纯青,画名驰誉京津,亦擅篆刻,辑《虽彝山房印存》)、陈恭甫(注:近代画家。名懿,以字行,居津门,张和庵弟子,工写菊,擅画时装人物,曾绘《桓华画报》)、陆文郁(注:1887—1974,字莘农,别署老辛,百蜨庵主。是天津现代著名花卉画家,也是著名的博物馆学家、植物学家和地方史学家。14岁从张和庵习花卉,书法。精花卉鱼虫写生,其画赋色艳丽,雅俗共赏。亦能诗。)为师。提及这段学习经历,他回忆说:“我二十岁学画时,天津有个指头画家,叫李石君。他是个有名的医生。这个人向来夜间画画,上午睡觉,下午出诊看病。我要跟他学画,怎么办?我白天工作,晚上睡点觉,夜里到他那儿学到天明,第二天回到家稍加休息,又去银行上早班,每天只能睡三几个钟头的觉。用今天的话说,这不是争分夺秒吗?”
曾见今人张金声有文是这样写的,“民国以降,津门擅指画且享大名者,前有李石君,后有梁崎,然王颂余亦擅指画,则鲜为人知。王氏名文绪,以字行,早岁忝列陈恭甫门墙,花鸟走兽山水,无一不精,无一不能。及陈氏殁后,王氏复入李石君门下,研习指画。李氏有“指圣”之称,王氏随其研习指画,一日千里,故李氏常与人谓:传其衣钵者,非此子莫属。其第一次参加中山公园画展获一等奖,好评如潮。王氏深谙指画精髓,然毕竟为小众所喜,且市场有限。后,王氏因身体违和等诸因,遂不做此技耳。其早岁之作,屡经劫难,亦鲜见于世也。”近日,曾见外公二十多岁时画的指头画(如图1),始信前言之不虚。
图1.颂馀先生1938年作品
对于颂馀先生艺术观与绘画道路选择影响至深的当属刘子久(注:刘子久(1891—1975),原名光城,号饮湖,天津人,人民美术教育家、博物学家。初学测量,继嗜国画。1920年在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学山水、花卉。1927年参加湖社画会,任导师。1937年以来任天津市美术馆秘书,创办国画研究班,从事国画创作和教学20余年。曾任天津市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追随其习画的时间与因缘,当属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进入其面向社会招生的“国画研究班”开始的。只是由于师徒二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相近,所以交往最深最久。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刘子久的带领下,在旧式山水画如何表现现实生活方面,展开积极的探索。二人既有合作,如《把物资运到祖国边疆》(1954年刘子久、王颂馀)(图2),也有独作《给军属拜年》(1951年/刘子久)(图3)《把余粮卖给国家》(1954年/王颂馀)(图4)。正是在追随老师的过程中,颂馀先生完成了由旧社会美术爱好者到新时代专职画家的根本性转变,并因其在那一时期的突出表现,与恩师刘子久同时在1960年被选为全国美协理事,由此跻身于名家之列。
图2.《把物资运到祖国边疆》
图3.《给军属拜年》
图4.《把余粮卖给国家》
正是因为有刘子久的提携栽培,再加之颂馀先生的自身努力,才逐渐受到新社会的肯定,在六十年代中期全国曾有过推选“人民艺术家”的评选活动,先外公作为河北省代表之一推荐到全国参评。虽然最后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此项评选不了了之。但是,此事却也说明他确实是属于转型比较成功的旧式文人画家。因此,颂馀先生不忘师恩,即便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动荡年代,也经常趋前拜望他的“刘老师”,笔者就有曾随之前往的记忆。
刘子久
溥儒
萧龙友
据先外公自述,他与溥儒(注:1896-1963,满族,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为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的师生之缘,是由被称之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家人的介绍。萧龙友(注:1870—1960,原名萧方骏,字龙友,号息翁、不息翁,四川省三台县人,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于1897年考中清朝丁酉科拔贡;1914年任财政部机要秘书等职;1928年弃官从医,在北京西城建“萧龙友医寓”;1930年与孔伯华自筹资金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与王家是较为熟识的医患关系,当其得知后生王颂馀喜爱绘事,因其女儿萧琼(注:1916-2001,又名重华,原籍四川省三台县,生于北平,著名书画家,著名中医兼书法家萧龙友之女,名画家蒋兆和之妻)正随溥儒习画,遂引荐之。由此就在往返京津两地学习的日程中,又增加了习画的安排。由于颂馀先生基本功较好,所以,很快溥儒就让其为山水画的代笔,笔者就曾在家中见过溥儒已题写好名款的空白画纸。虽说此种行为为后来的书画鉴定带来许多麻烦,但是也说明溥儒对这个弟子画技的肯定。
而说起他去溥儒老师处学习时,则说到每次去后,如果没有问题,就只是站在一旁看老师作画,停笔闲聊时,也多是诗文之类,如果不提问,一般是不会主动传授绘画技巧技能的。这是因为溥儒认为“听讲授不如看画画,一切言语尽在画中”,要求学生按照他画的画去画即可,即便是讲,也很少就画论画,更多的是谈国学。不过,无论是作画还是谈学问,溥心畬所围绕的中心是始终明确的,那就是要无条件地向传统学习。学生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机会提问,溥心畬回答也多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外公在跟随溥心畬学画期间,就是遍临古代经典。正是这样的学习经历,给外公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外公还曾不止一次地跟笔者提起他在溥宅观赏溥心畬与张大千合作绘画的感受,称其终生难忘。
家母回忆,她记得小时候曾经家中上下全员耗费几天的工夫收拾房间,大人说是准备迎接溥儒来家中做客。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满清旧王爷兼老师要来普通人家中做客,可谓大事。没成想当天不知何故溥儒没来,来的是一位雍容华贵派头十足还有点傲慢的年轻妇人,后来先外婆告诉家母来的是溥儒的姨太太,其实她说的是李墨云。家舅也跟笔者说过,正在北京燕京大学上学的他曾替父亲去给溥儒送还借来的画册,溥儒让他带回天津两只毛茸茸小鸡给弟妹们玩的事情。
记得1990年代笔者初到日本后,跟友人聊起外公王颂馀的书画老师分别是溥儒与溥修(注:1896-1956,字仲业,号默公。满族,清宗室,其父载濂为道光帝嫡孙。末代皇帝溥仪以同族关系,曾托溥修代为照料天津的私产。不曾出任任何职务。擅长诗文书画。1955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对方纳闷他究竟是何种机缘得以拜两位溥氏为师,本人也无言以对。趁着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仔细询问了先外公。他说是1940年代的某年溥儒率一众弟子在天津办画展,时居天津的堂兄弟溥修也来观展,跟他谈论起先外公画上题款的书法不错,于是溥儒就把肃立在侧的王颂馀介绍给溥修,要其跟从溥修学习书法。
溥修
颂馀先生对笔者说过,溥默公的书法教学方式很具有新意。他要求外公每次到其家中求教时不得自带毛笔,而是每次都从自己的笔筒里拿出不同的毛笔来让外公练习,其目的是为了掌握不同毛笔的笔性,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外公逐步掌握了使笔而不为笔所使的本领,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任何种类的毛笔。另外,溥默公还经常要求他针对一个字要书写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结字方式,而这种练习又为外公书法方面的衰年变法时在结字与章法上得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跟随溥默公学习书法的同时,外公还在其指导下开始了对佛学的学习。
据先外公说,溥修长期在津,先是为溥仪在津期间的财务主管,溥仪离津后,又代其料理在津私产。后来,因时局益发动荡,生活逐渐拮据,不巧罹患眼疾,是外公在人力物力以及就医方面给予关照。他为表达谢意,将家中所藏一套故宫藏画图册赠与王颂馀。1950年代溥修返京度晚年。
而有关这套图册的由来,颂馀先生则又不得不说一段轶事。他说有一年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为了给日本献媚,借为昭和天皇过生日的机会,想从他带到东北的故宫藏画中选出一批作品在日本举办一个展览。他担心此批作品展后被扣留不还,所以事先拍了珂罗版底片,以防万一。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此展览告吹。1960年代故宫博物院来人有意收购此套图册时,先外公方得之,当初该底片洗印了三套照片,并装订成册,至今,一套在沈阳故宫,半套在北京故宫,另一套即在我家。因此图册是恩师馈赠之物,先外公自然是不肯转让。虽说此图册并非原作,但因连年战争与动乱,这批画作难免有个别作品的遗失损坏,故其文献价值还是不可低估的。
原本从事了二十多年金融工作,在工作之余兼修诗文书画的王颂馀,如果不是1950年代初期从银行的被退职,也就不会有后来将爱好当职业的成功转型;如果没有恩师刘子久的引领与提携,也就不会有用旧山水画表现新生活的努力尝试;如果没有自身紧随时代的多件创作,也就不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多方认可。于是,当年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转身而为美术工作者和美术教育者,最后成为了奠定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成为了著名的书画家。
也正是源于这个变故,起初不过是将研习书画当做一种文化修养的王颂馀,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因客观的变化与主观的努力,书画的研究、创作与教学不但逐渐成为了“生活状态”,最后更是成为一种“生存状态”。
如此的人生变化,恐怕是先外公所始料不及的。
(来源:公号建十聊书画)炒股配资论坛大全
发布于:天津市融丰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